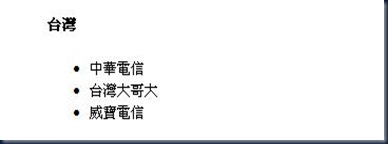那天,和M一起去逛街,偶然間聽到路邊一間小小的服飾店放著我最愛的搖滾樂團Linkin Park的歌,我抵擋不住音樂的誘惑,拉著M走進店裡,沒兩分鐘就在店裡買了一件衣服。「你瘋了嗎?就因為聽到音樂而買衣服?」M用很不可思議的表情看著我。「我才沒瘋呢,我聽到我喜歡的音樂所以心情很好,在讓人心情好的店裡買衣服不是很正常嗎?而且我可沒亂買!這件衣服我還滿喜歡的。」我理直氣壯的回嘴。
後來逛街的時候,我開始沒辦法專心購物,思緒時不時地掉進過往回憶的漩渦,那些畫面不甚連貫卻又清晰至極……
我看到我坐在高中同學胖達的位子上,用他的隨身聽第一次聽到Linkin Park的歌,我仍然記得那首歌是第二張專輯Metora(天空之城—美特拉)裡面的Somewhere I Belong(我的歸屬)。我依然記得主唱Chester雄渾且暴力的嘶吼嗓音是如何一字一句的撞擊我的靈魂。至今,我依舊記得當聽完整首歌時,身體如何因為那些似懂非懂的歌詞產生的感動而幾近虛脫。
於是在那苦悶且青澀的高中住宿歲月裡,我為我的靈魂找到了宣洩的出口。
毫無意外的,我跟隨著胖達的腳步一起變成了Linkin Park的歌迷。作為前輩,他向我說了許多這個樂團的故事,像是主唱Chester悲慘的童年,充滿陰霾、挫折的成長過程,樂團裡面其他人如何認識Chester、包容他、關愛他、幫助他脫離毒品和酒精的糾纏,以及和他變成真正互相關心的朋友,這個故事就讓我非常感動。
很多人在知道我對於Linkin Park的喜愛幾近於狂熱之後,都會問我為什麼。不擅長言語的我通常只是笑著說,喜歡上了就沒辦法了啊,但其實我真正想說的是:每當我聽過一遍CD,裡面的任何一首歌都像是一顆炸彈,它們挾帶著強大的能量轟炸我心靈的每一處,把我內心的渴望、不捨、憎恨、憤怒、怨恨、無奈等等的負面情緒全都炸上了天,再重重的摔下地化為塵土,於是我才能夠細細審視那些佈滿在心靈深處的傷口。就某種層面來說,Linkin Park的音樂就是我的自白劑,在他們的音樂裡,我對自己沒有謊言,只有我與我的靈魂真誠的面對面。
我想起了在那個單調的高中住宿生活裡,每天經過許多考卷的疲勞轟炸之後,最令人渴望的時刻就是洗好澡坐在書桌前,讓Linkin Park的音樂隨著隨身聽的耳機直達耳膜,喚醒因為考試而逐漸麻痺的思緒。Chester的嗓音對我來說有一種叛逆的特質。潛藏在他的嘶吼之下,是他對這個世界的渴望和要求,他用他的聲音明白地向全世界訴說他想要什麼、他正抗拒著什麼。於是他的聲音逐漸變成我的信仰和勇氣的來源,藉由這個樂團的音樂,我開始相信我能夠極力爭取我所想要的一切,而不是任憑他人擺佈。
我想起了我曾在總是一成不變的教室裡面看著窗外,腦裡不斷重複播放著Easier To Run(說逃就逃)這首歌。儘管它的歌詞所描寫的情境和我的心境並不契合,但是我發現,只要讓腦袋一直重複這首歌,我的思緒就可以輕易的隨著旋律迴旋反覆地衝破天際,在一片海闊天空中翱翔。在這首歌裡,我得到了暫時而寶貴的翅膀。在那片想像中的湛藍天空裡,有著一種孤獨的甜瀰漫在空氣中。
我想起了從前有一段時間,父母的爭執使家裡的每個人都不得安寧。當我唯一的避風港都開始破敗,在內部颳起不見天日的狂風暴雨時,我開始懷疑我的歸屬在何處。我只能一次又一次,重重地摔上門,讓Somewhere I Belong這首歌強勁的節奏在我身邊圍繞成一個讓我不至於淹死的救生圈,我在房間裡面隨著強而有力的鼓聲載浮載沉,濕漉漉地等待救贖。
我想起曾經有一個我喜歡的女孩恣意妄為地揮霍我對她的信任感。當我發現事實後,我讓From The Inside(發自內心)這首歌的歌詞和我的憤怒完美契合地嘶吼宣洩。”Take everything from the inside / And throw it all away / Cause I swear for the last time / I won’t trust myself with you / I won’t waste myself on you!!! / You!!! / You!!! / Waste myself on you!!! / You!!! / You!!!”這幾個簡單的句子在那些充滿酸澀液體的日子裡代替了一切充滿惡意的話語和舉動,我告訴自己,至少我能夠理性地做到不要再浪費生命在她身上。
我想起從高中畢業的那個暑假開始,我都會在鐵工廠裡用至少兩個月的汗水和傷痕換取之後上大學的生活所需。每天都是同樣的過程。七點起床,八點上班,十二點吃飯,五點半下班。不同的只有每天下班之後,帶回家的程度不一的疲累。有如寫壞的電腦程式一般,一再跑著同樣的迴圈。 日復一日,溽暑的烈日、紛飛的鐵屑、電焊的強光不僅刻蝕著我的皮膚,更消磨著我的心智。在那樣的日子裡,唯一支持我的只有腦裡不斷自動迴響的Crawling(爬行)的歌詞:”Crawling in my skin / These wounds, they will not heal / Fear is how I fall / Confusing what is real……”Chester獨特的沙啞嗓音完美地詮釋我身上的傷口,在那些加總起來約兩百多個的日子裡,他的聲音就像是我的拐杖,讓我雖然孱弱卻依然能夠踽踽獨行。
上了大學之後,我的眼界較之前更廣,內心關注的對象從自身逐漸擴充到這個世界。就在那一年,Linkin Park也推出了睽違四年之久的第三張專輯”Minutes to midnight”(末日警鐘—毀滅.新生)。我訝異地發現,他們的音樂像是跟著我一同成長一般,他們不再只是對世界滿懷憤愾的要求什麼、抵抗什麼,而是轉而希望聽眾能夠跟著一起關懷周遭的人以至於整個世界。在這張專輯裡面,不同於以往的是曲風大幅度降低從前那種充滿情緒的力道,代之以溫柔但尖銳的立場,批判著許多社會現象。從最先釋出的單曲What I've Done (過去的我)的音樂錄影帶就可預先窺見他們的改變,他們用很多令人怵目驚心的影像讓觀眾產生警惕:國際戰爭、流血暴動、血腥鎮壓、貧窮國家的食物匱乏、富裕國家的奢侈舖張、環境污染、獨裁統治者的謊言、毒品氾濫、核子威脅……等等,那些影像都是真實在世界上各個角落發生過的,也因此讓觀眾難以忽略他們的訴求。另外像是The Little Things Give You Away(由小見大),這首歌是Linkin Park在訪問過遭受卡翠納風災襲擊的紐奧良之後所作,在Chester的詮釋之下,整首歌透出冷冽卻又溫柔的氣韻,緩慢道出災民的傷痛與堅強。
大二那年,Linkin Park首度來台舉辦演唱會,我用暑假賺來的薪水買了一張門票,在期中考的前兩週以朝聖的心情從嘉義搭車前往台北中山足球場,加入了那場和四萬人集體瘋狂的演唱會。至今我都還能夠記得當天從中午開始排隊,排到晚上七點進場時,我的腎上腺素如何支持著我因為趕車而疲累的身軀;我也還記得,當Linkin Park從舞台上現身時,全場觀眾的歡呼是如何震動著大地;我更記得我是如何跟著他們的曲子毫不顧忌他人眼光地擺動身軀、狂吼歌詞,以至於接下來的好幾天我筋骨酸痛、難以講話。就如同伊斯蘭教徒視麥加為聖地而希望一生至少能夠前去膜拜一次,我對於參加那年的演唱會也抱持著相同的想法。人的一生能有幾次像這樣不顧一切的瘋狂呢?人的一生能有幾次像這樣近距離地觸碰已扶持自己許多年的偶像呢?當我將來上了年紀回憶起這段年輕歲月,我會不會後悔沒去參加過他們的演唱會呢?第一個問題和第二個問題,我當然沒有答案,畢竟我還年輕,未來的路還很長遠,遙遠的路上會發生什麼全都讓人不敢確定。但是針對第三個問題,我很肯定我若是沒有參加過那場演唱會,我必定會非常懊悔,因為我親手放棄了一個體驗人生的機會。
我想我和世界上許許多多不認識的人會如此喜愛Linkin Park的音樂,是因為我們經歷過,或是正在體驗人在某種年紀獨有的哀愁與惆悵。這種哀愁與惆悵就像七彩的泥漿漸漸地灌入我們本來透明的靈魂。有些人因為受不了而窒息,提早在這個世界退場;有些人學會讓那些泥漿變成理性的沈澱物,然後他們默默地成為大人。剩下的人則是想盡辦法排除那些泥漿,極端一點的人用飆車、打架、蹺家等等方法嘗試將靈魂撞出一個大洞;較溫和的人則用音樂、圖畫、文字一點一點的將靈魂敲開。就目的而言,這些方法都沒有什麼不同,都是為了保護自己天生的清淨澄明不讓那些七彩泥漿佔據,但有些人卻在不自覺間慢慢的被染黑。許多大人因為害怕黑,於是彷彿刻意忘記了自己也曾經歷過那樣的年紀,著急地將那個年紀的我們統稱為叛逆。理所當然的,「叛逆」成為我們在那個年紀的專利罪名。我們「叛」的是兒童時期的乖巧,「逆」的是長輩的期許。那個年紀的我們身處於夾縫當中,身心都已經與孩童時期有了決定性的改變,卻又不想變成那些我們眼中勞碌不堪的大人,於是我們獨樹一格地標榜自己的個性,積極定義自身與世界的關係。在這些過程中,我們難免因為行動充滿攻擊性以至於常會受到來自大人的阻撓與挫折,我們不免因為那些挫折與阻撓而感到灰心、憤怒,甚至懷疑我們存在的意義何在。於是Linkin Park的出現,順理成章地成為在這個年代裡,我們這些叛逆之人的靈魂出口。他們的歌曲精確地唱出我們渴望讓這個世界瞭解的一切想法與不滿,卻又不帶任何一個髒字,於是我們被他們折服,讓他們成為我們的信仰以及支柱,我們因此擁有足夠的勇氣在這個世界橫衝直撞,就算受傷也能獲得慰藉,就算挫敗也能大聲宣洩。
如今的我似乎已經脫離了那段一個人一生中最多彩寶貴的階段,逐步地變成一個大人該有的樣子:理性、智慧地處理每件生活中的大小事,但我也開始害怕我會因為成長而漸漸失去我所擁有的熱情,於是即使已經不再叛逆,我依然聽著Linkin Park,讓Chester的歌聲為我保持那些我希望能夠一輩子保留的特質。值得慶幸的是,我相信Linkin Park會繼續成長下去,讓我能夠繼續為我和這個世界的關係定下嶄新的定義,繼續在音樂的引導之下找尋未來的歸屬。